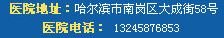“津市望江楼曾是澧水流域临江最高、最恢宏的楼,也是小吃的集大成者。”作家龚曙光在游船上望着津市两岸,感慨道。
四十多年前,他就是从望江楼的码头登船,外出求学。彼时的津市,还是澧水上的重要中转站,舟楫往来,码头上热闹非凡,登船远行的人们,总要买上几个望江楼的包子。
“望江楼最出名的是北方的面点。”津市的美食,从来就不只是米粉。韩少功、水运宪、蔡测海、阎真、王平、龚曙光、沈念、李卓八位作家,在9月13日开启津市采风之行。这是一次作家采风之旅,更是一次寻味之旅。
在作家们看来,津市的美食里,藏着这座城市最真实的历史和精神。
韩少功:津市牛肉粉和鲊辣椒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理符号
津市本身就是一个“市”,它的城市化程度是很高的,城市化进程早就开始了,工业基础好;而且,它也是古老文明的原乡,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就是最开始显露文明的曙光的地方。昨天我还开玩笑说,这里的人,在文化上的辈分是很高的。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妈妈来过津市两次,那时候是坐船。半夜在长沙上船,要到第二天的傍晚到津市。那时候觉得津市很遥远。
我的祖籍地在澧县小渡口,离津市很近的地方,所以,津市其实也是我的祖籍地,我从父辈那里经常听到津市这个地名。小时候,母亲的厨房里,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样,一个是牛肉米粉,还有一个是鲊辣椒,特别是用鲊辣椒做那个小鱼的糊糊,味道特别鲜美。现在一年能够吃到一两次鲊辣椒,就不容易了,偶尔在餐馆碰到,我都觉得很亲切。鲊辣椒对我来说,不是简单的食品,而是心理符号,它承载着我的很多童年记忆,有很多来自父辈的、家庭的隐秘信息在里面。
在津市我感到特别亲切,满耳朵都是我老爸老妈说的那些话、那些声音。但我儿时的那些印象,现在的津市完全没有了。我昨天很想找当年的码头在哪里,我在哪里上的岸、在哪个小粉店吃的米粉,都找不到了——声音还在,但是景观变了,这给我的感觉特别奇妙。
米粉的味道,感觉也和小时候不一样,我在怀疑是不是这么多年我自己的口味变化了,而米粉和其他美食的味道其实一直没变?这里是有一个问号的。
水运宪:津市的发展颠覆了我以前的记忆
津市来过很多次,但是沉下心来待几天,还是第一次。津市,在我原来的印象当中,就是因为水路运输码头而生成的一个集市,一个集镇,吊脚楼、码头啊,那些我都看过;现在感觉到津市已经有点颠覆我以前的记忆,津市港一期二期的现代化建设规模超乎我的想象。
我们都知道农耕文明时代,我们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都是靠水路运输。今天水路运输相对我们现代化的大交通、大物流是比较落后了。但是,在津市,我觉得它反而超前了——从城市发展的经济学角度来讲,可能这更适合经济发展。
我在常德长大,我原来知道常德的餐饮,包括零食啊,还是不错的,在全省都很有特点。这次来才发现,比较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饮食产业,在津市,而不在常德市。
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们在长沙就已经感觉到了,像刘聋子米粉,在长沙有十几家,它不管是米粉,还包括它的作料、它的汤料,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化,这个非常了不起。产业化的生产,必须是根据市场来的,说明我们津市的饮食市场也是十分广大的。
在我几十年前的印象当中,津市的工业就很有特点。我不知道那些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湖南拖拉机厂、湘澧盐矿,还有在香港都非常有名的斑马蚊香——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广州二沙头,看到有个商店门口就写“好消息,今天有斑马蚊香”,它还缺货。
所以津市这个地方很神奇,地方很小,人口很少,闷声不响地在这里走自己的路,憋大招,我觉得这个地方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大爆发,什么时候不好说,但看来势就是这样的,实实在在做事,一心一意谋发展,我对津市充满了期望。
蔡测海:我的认识,其实是好几代人的认识
津市,津,水边嘛,我老家是龙山的,津市是我从老家出来后,第一个大的口岸,当时称小南京。我对津市的认识,其实是好几代人的认识。我的先辈,从山区出来,把木材在常德或津市卖掉,再买上些生活用品回来。到我们年轻时候,津市的斑马蚊香全国很有名。现在,津市的米粉,由一个老品牌做成了大品牌;津市的一些小吃、点心做成了现代化的食品产业,既有传统的味道,又有现代的工艺和科技含量,而且规模化。把一种原本只是本地的饮食,推向了全国。
说到美食,常德和我们湘西一样属于大西南的范围,它的菜有着大西南的风味。我看这里的美食,包括米粉,也放花椒,我们湘西也放,但我觉得它和湘西相比,它辣得没那么辣,麻的也没那么麻,油也没那么油,它更平和一些,不像山区那样性格猛烈,所以,它更容易让外面的人接受一些。我说不出哪道菜更好吃,我觉得他们所有美食都讲究品质,做得都很认真,都好吃,都对我的口味。
阎真:这里是一个非常滋养人的地方
我觉得津市是个很有特点的城市。它的历史悠久,和它的地域也很有关系。我们的先祖生产力很低下,必须靠好的自然条件才能生活——我们昨天参观了津市市博物馆,看到远古时代,这里就有很多人类活动的踪迹,深感津市是一个非常滋养人的地方。
这里的人有利用自然资源的禀赋,有讲究吃的基础和传统。这个基础和传统,被今天的津市人发扬光大,大菜和小吃都做到了极致。我希望津市的美食能够做到像沙县小吃那样,走向全国,到处开枝散叶,从它的美食传统和资源条件来看,是有这个基础和实力的。
我比较喜欢吃甜食和味道香的美食,这次来,除了牛肉米粉,我印象最深的是油糍饼和油坨。我在长沙没吃到过油糍饼。油坨我在别的地方吃到过,但这里是我吃到的最好吃的,别的地方炸出来的黄,颜色很深,它是淡淡的黄,特别好看,也特别好吃。很多东西是大同小异,但它就好那么一点,感觉就不一样,做到了极致就不一样。
王平:猪大肠油渣子味道有点奇妙
以前一讲起津市,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遍布长沙大街小巷的津市米粉,尤其是刘聋子米粉。我亲眼目睹了一家津市米粉在长沙奋斗最后落根的过程。那是在望月湖,上世纪90年代初,津市牛肉米粉最初到长沙的时候,一对津市夫妻来长沙创业。开始每天只卖得两三碗,后来店里坐不下了。所以,我想,津市米粉在长沙、甚至在湖南,乃至全国,应该是有它的品牌竞争力的。
这次来,印象更加深刻,尤其是今天早上,在刘聋子粉店的本店,大长见识——有那样琳琅满目的津市小吃,而且样样口味独特。讲起吃,今天中午的猪大肠油渣子,是我头一次吃到,又酥又脆,又有点糯,它的味道有点奇妙。油渣子其实是很普通的一道菜,居然炒出了这样味道,真是妙不可言。
这次澧水乘船浏览,看到他们对航运的追求和理想,非常打动人心。特别是听说澧水疏浚之后,到达松滋口,水运将近节约多公里的水程,这个计划如果真的实现,将对津市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好处。我是期待津市有更大的发展的。
龚曙光:津市美食承载了澧阳平原对待大地、对待人生的态度
津市对我来讲不陌生。我出生在这个地方,我的父母也在这个城里生活了几十年。
每次回津市,注意到它有变化很快的地方,也有它始终不变的地方。那些很快的变化,有些令我欣慰,当然也有些令我焦虑;反倒是那些不变的地方,它永远吸引着我,让我不厌其烦地、坚定不移地去探索它——比方说它作为澧水流域最早发达的小城市,承载了整个澧阳平原上的人文地理,它甚至代表了澧阳平原几千年以来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以及态度和方式所积淀的文明成果。
这次我们来主要是采访津市的食品业,通俗来讲,就是采访和了解津市的吃。实际上,津市的吃,就是澧阳平原列祖列宗在他们生息繁衍中所积淀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体。它既代表了我们祖先对待大地、对待命运、对待人生的态度,也代表了这块土地,对待四面八方所传递来的物质文化的态度。
我们今天很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yf/6123.html